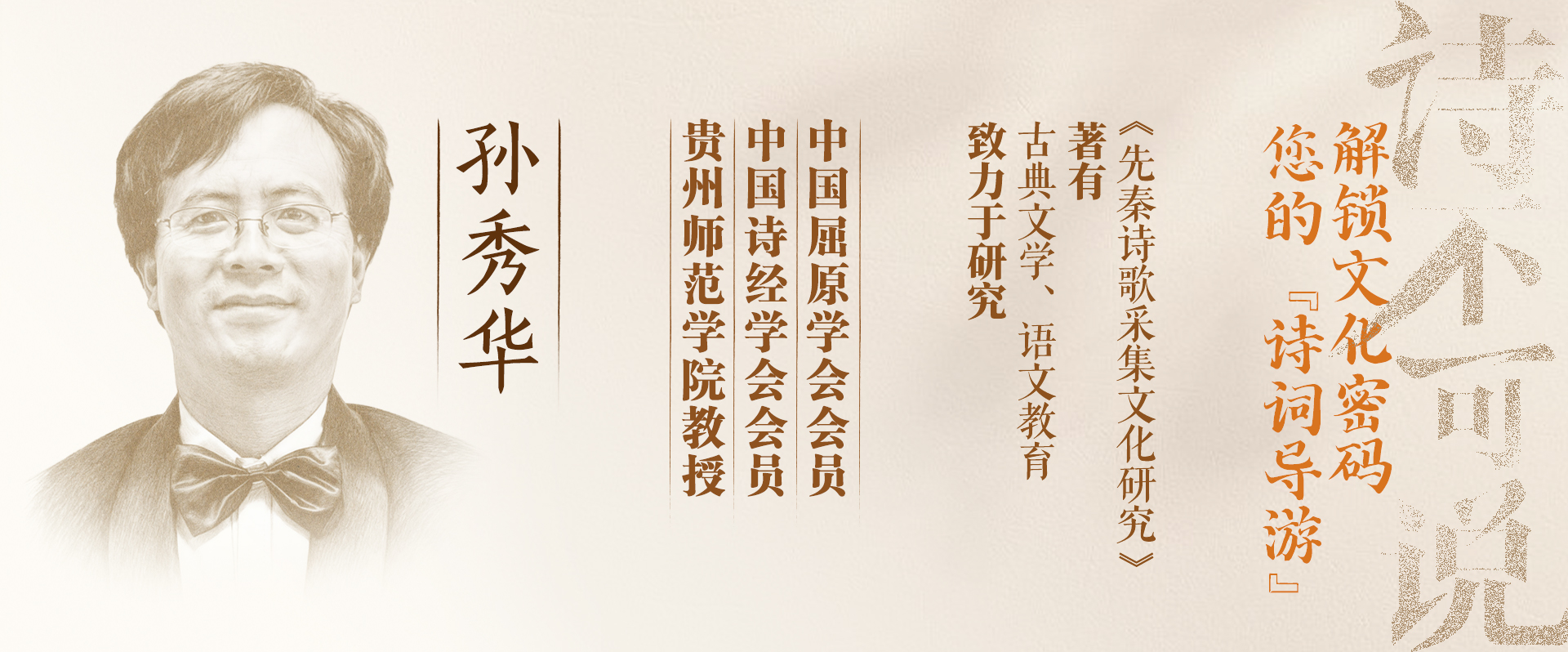
“烟波画出暮江天,著我芦花明月船。”宋代文士笔下,明月与芦花组合为独特唯美的意象,凝聚了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趣味。浩渺江天,芦花在明月的清辉中摇曳,仿佛沉浸在虚无缥缈的空灵境界,却又透露出在动荡与飘摇里寻找精神安宁的坚韧。芦花的朴素淡泊与明月的高远澄明,共同构筑了纯洁的心灵栖息之地。
初唐陈元光《候夜行师七唱·其五》有“明月芦花迷曲岸,西风梧叶报清秋”之唱词,但真正最早把“芦花明月”赋予整体象征意义的是五代名僧贯休。贯休《秋末寄武昌一公》诗曰:
见说武昌江上住,柏枯槐朽战时风。
知师诗癖难医也,霜洒芦花明月中。
贯休是著名的诗僧,贯休卒后,其诗文被弟子昙域集为《禅月集》三十卷,今本存诗二十五卷,佚去文五卷。《全唐诗》编贯休诗十二卷。吴融《禅月集序》称赞说:“(贯休)上人之作,多以理胜,复能创新意,其语往往得景物于混茫之际,然其旨归必合于道。”贯休这首《秋末寄武昌一公》诗,结语“霜洒芦花明月中”尤为出色,诗中有画,冷峻高洁,清幽静谧,灵动缥缈。
其后,北宋释重显以唯美的“明月芦花”意境来谈禅说法。释重显《颂一百则·其六十三》歌云:
看看,古岸何人把钓竿?
云冉冉,水漫漫,明月芦花君自看。
“明月芦花君自看”作为“禅语”,见于南宋释普济编纂《五灯会元》卷十四:“僧问:‘如何是透法身句?’师曰:‘铁牛放去无踪迹,明月芦花君自看。’”千斤万斤的铁牛走在地上如何“无迹”呢,或正如你心头的千万斤重负焦虑一旦“释放”“释去”,则自然会感觉空明轻盈,恰如同那皎洁明月下的洁白芦花,在风中摇曳。谈禅的机锋便是如此,这或许就是禅宗的“空无”观念吧。而从普遍意义上讲,这里的“明月芦花”代表着不可捉摸、虚无缥缈的禅意,是超越言语和思维的直觉体验,促使人们超越凡俗,在悲喜与动荡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豁达。
而芦花与佛教结缘不浅。达摩“一苇以航”的佛教典故,象征修行者通过虔诚信念与智慧超越障碍,抵达觉悟彼岸。佛教将芦花视为“无尘之植”,白色芦花与挺拔姿态寓意修行者需保持内心纯净,超越尘世纷扰,达到“清净妙明”的精神境界——如此境地,正是“明月芦花”“芦花明月”。
北宋释道全《题林景思权巢·其一》诗曰:
不嫌茅把盖头低,为爱平檐野雪迷。
自与芦花梦明月,夜寒空误鹤来栖。
诗中的“自与芦花梦明月”,更是诗家俊逸之语,清洁无尘,高妙蕴藉。
北宋释清远有云:“白云消散青山在,明月芦花对蓼红。”北宋释怀深有曰:“明月芦花藏不得,老来重跨铁麒麟。”北宋释正觉有云:“芦花明月阿谁事,人在江湖把钓竿。”两宋间的释可观《颂古》诗曰:
夹山不在一桡上,明月芦花夜夜寒。
谁谓华亭消息断,俨然秋色在江山。
之后,以“明月芦花”来“说法”的意味更为明显的,有南宋释师范《偈颂七十六首·其五十二》:
现成公案,何事不办。
百发百中,无边无畔。
捏不聚,拨不散。
万籁俱沉兮明月半窗,一色难分兮芦花两岸。
因果报应,“百发百中”,虽然是在“说法”,最后两句却也是诗意盎然,意境清冷,发人深省。
宋代文人写明月芦花,呈现出朴素的自然之美,完美表达了芦花与明月的视觉诗意。如北宋钱易《芦花》诗有云:“凝洁月华临静夜,一丛丛盖钓鱼船。”明月、静夜,一丛丛的洁白芦花、隐隐约约的钓鱼船。月光使芦花更显洁白,芦花则让月光更添温柔……恬静安然,如梦如幻。如此的“闲梦”,恍惚一线牵,让人回想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“芦花明月”小词。李煜《望江南·闲梦远二首·其二》词曰:“闲梦远,南国正清秋。千里江山寒色远,芦花深处泊孤舟,笛在月明楼。”
北宋苏庠《清江曲·其一》歌云:
属玉双飞水满塘,菰蒲深处浴鸳鸯。
白蘋满棹归来晚,秋著芦花一岸霜。
扁舟系岸依林樾,萧萧两鬓吹华发。
万事不理醉复醒,长占烟波弄明月。
苏庠写芦花与明月,是分说的。“秋著芦花一岸霜”,隐士情怀,居然不说“秋著芦花两岸霜”,单单眼里只有自己的这以岸边了。而上句“白蘋满棹归来晚”暗示了明月的存在。果然,结语说“长占烟波弄明月”,画面也丰满明亮了起来。
苏轼对苏庠的这首《清江曲》大加赞赏,说是可与李白李太白之作媲美。苏庠字养直,号后湖居士。“少能诗,苏轼见其《清江曲》,大爱之。”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六十八载曰:“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,谁复疑其非也。乃吾宗养直所作《清江曲》云。”
而最受宋代文人追捧的明月芦花意象创造,是来自黄庭坚的“满船明月卧芦花”。在苏轼发起的关于“薄薄酒”的诗歌唱和中,黄庭坚《薄薄酒二章·其二》有曰:“何如一身无四壁,满船明月卧芦花。”确属高格凌云,清逸峻拔。
南宋陈文蔚《庐陵于两池中作船亭,名“卧芦”,取山谷“满船明月卧芦花”之句。落成为赋小诗》云:
路入芳池柳岸行,宛然野渡一舟横。
祗缘胸次规模别,便有江湖气象生。
云影恍疑帆影度,啸歌中有棹歌声。
天书恐逐衔芦雁,未许花边卧月明。
“明月芦花,共是江南客。”其后,南宋方岳、萧立之对于黄庭坚黄山谷之“满船明月卧芦花”名句也有致敬之作。方岳《陪吴总侍集研山用赵端明送行韵》有曰:“烟波画出暮江天,著我芦花明月船。”南宋萧立之《送厚斋陈持正归括苍效山谷体有赠》有云:“夜深拥被蝴蝶床,满身明月卧芦花。”
“明月芦花醉眠”,南宋孙应时看到了苏轼苏东坡的画作,有感而发,也有一首“明月芦花”小诗。孙应时《题光福刘伯祥所藏东坡枯木及渔村落照图·其二》诗曰:
夕阳雁影江天,明月芦花醉眠。
乞我烟波一叶,伴君西塞山边。
这首诗对应所写的是苏轼《渔村落照图》,诗歌内容却当与画作画面不尽相符。“落照”即夕阳,画面应该是渔村晚霞景象。但苏轼画作或不是“丹青”而是文人水墨,落日也许很容易被看成“明月”或故意误认为“明月”,故而才有“明月芦花醉眠”之歌咏。
“满江明月芦花秋”,宋代文士写尽了秋意与孤寂,倒也一往情深,潇潇洒洒。南宋张同甫《秋日忆友》诗云:“阊阖风高白露秋,芦花如雪动边愁。故人迢递天南北,明月娟娟独倚楼。”诗作表达了对朋友的深切思念,以芦花明月为背景,但芦花明月其实甚至已成为一种孤寂感的外化标识。
“满船明月芦花白”,“芦花影里弄明月”。南宋施枢《泛月夜归》诗云:
短艇冲寒泛浅沙,满溪明月浸芦花。
忽惊远岸灯光发,篱落萧疏一两家。
明月芦花,是宋代文士最爱的唯美意象之一。宋代文人通过对明月芦花这一自然景致的审美体验和艺术表达,构建了一个融合视觉美感、情感共鸣与哲学思考的丰富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,他们找到了精神的栖居地和心灵的慰藉所。当我们重新审视明月芦花这一唯美意象,不仅是为了了解宋代文人的审美趣味,更是为了寻找一种在当今社会中可能遗失的生活智慧和生命态度。或许,不经意间,在某个清冷的秋夜,当我们面对明月下的芦花时,也能感受到宋代文人所曾经体验过的那份宁静与超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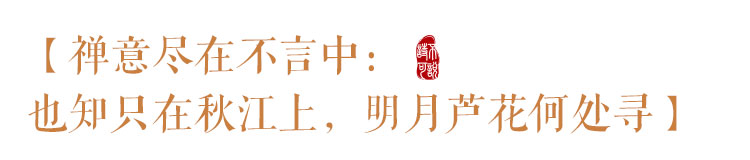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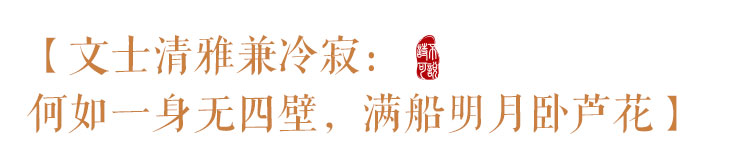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— 热门评论 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