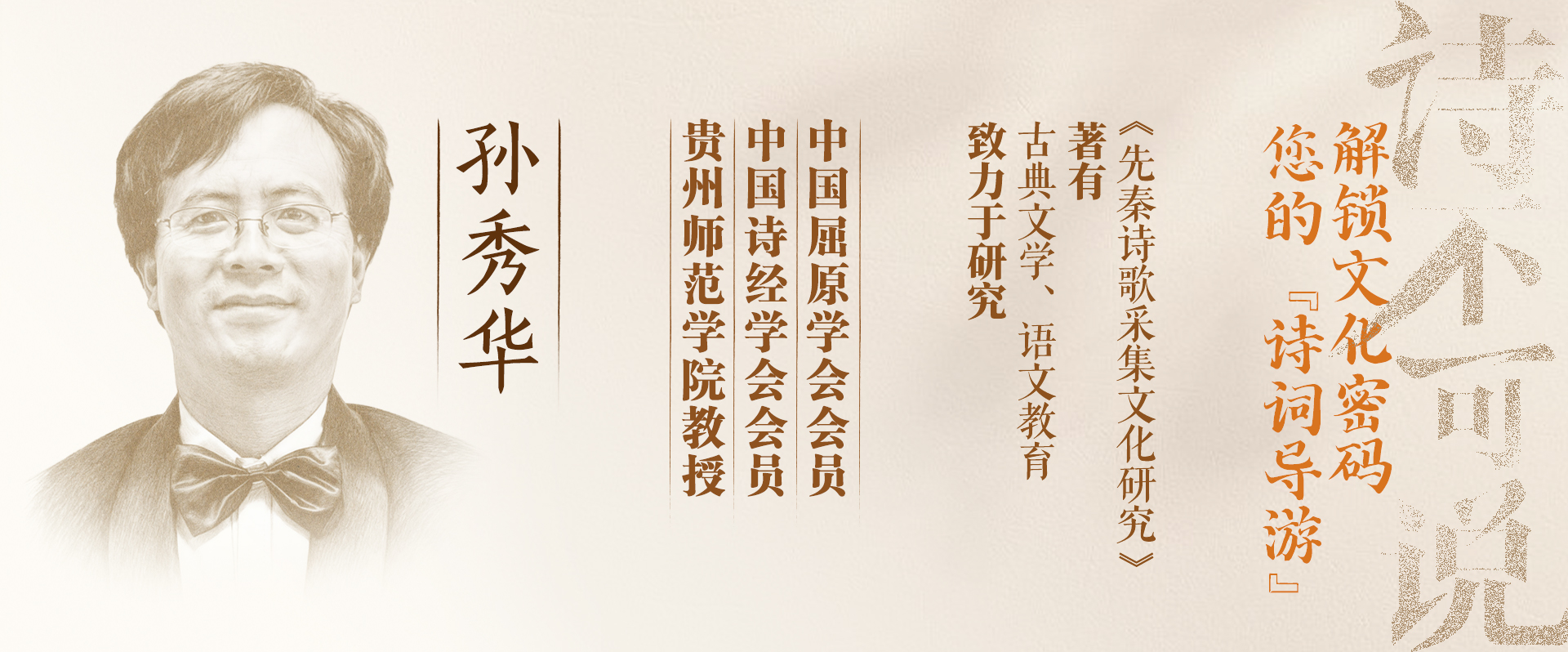
春花秋月,夜风轻拂,古代文人的“露坐”仪式与“露坐诗词”,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。
早期的“露坐诗”,中晚唐时代的马戴写有两首,较为人称道。马戴《春日寻浐川王处士》诗曰:
碧草径微断,白云扉晚开。
罢琴松韵发,鉴水月光来。
宿鸟排花动,樵童浇竹回。
与君同露坐,涧石拂青苔。
诗作写与友人月下露坐,弹琴清冷,春花宿鸟,碧草松竹,涧石青苔,无不高洁清雅……对于这首诗,《唐诗摘钞》赞赏说:“全篇幽淡雅润,句法、字法、章法无不入妙。若在盛唐,几与右丞争席矣。”文句中的“右丞”指王右丞王维,王维官至尚书右丞,故有此称。而如此评论马戴的这首诗,是认为马戴诗作可与王维的诗歌并肩而立不相上下了。
马戴另一首也写了“露坐”的诗歌是《田氏南楼对月》,诗有云:“主人同露坐,明月在高台。”写身处主人家的南楼上,饮酒赏月,与田氏主人共同“露坐”,情深意切之外,透露着明显的仪式感。
“露坐”的字面意思就是露天而坐,但古代文人笔下的“露坐”或源自佛教头陀苦行的“露地坐”,或者至少受到了佛教徒“露地坐”行为的影响。
著名的唐代诗僧寒山便写到了修行意味满满的“露地坐”。寒山《诗三百三首·其二百五十三》诗云:
余劝诸稚子,急离火宅中。
三车在门外,载你免飘蓬。
露地四衢坐,当天万事空。
十方无上下,来去任西东。
若得个中意,纵横处处通。
据《佛说十二头陀经》及《十住毗婆沙论》等经典,露地坐,是佛教头陀行的一种修行方式,旨在舍弃世间贪欲,磨炼行者的意志,与佛教空性理念相应,修行者可以领悟佛法真谛,消除烦恼,证得无生法忍,最终达到解脱境界。
见录于《敦煌歌辞总编》卷三,有首敦煌曲子《空无主》,明确唱到了“无碍解脱露地坐”。唐代敦煌曲子《空无主》歌曰:
身心无知如空虚,众生颠倒以为我。
善恶是非诸见网,如蚕吐丝自缠裹。
奇灾祸。
何时打破烦恼舍?无碍解脱露地坐。
断枷锁,实难可。
五阴大贼本清凉。云何不觉火中坐?
这是劝人向佛的“曲子词”,慨叹世事如网空自缚,善恶颠倒皆灾祸。而如何打断枷锁打破烦恼呢?当然要靠苦修的“露地坐”了。
而比马戴生活时代要早的中唐时期,李端与韩愈其实已经写到了“露坐”。李端《送惟良上人归润州》诗曰:
拟诗偏不类,又送上人归。
寄世同高鹤,寻仙称坏衣。
雨行江草短,露坐海帆稀。
正被空门缚,临岐乞解围。
“上人”是对佛教僧侣的尊称,特指持戒严格且精通佛学的高德僧人。李端该诗所送别要回到润州(今江苏镇江)的是“惟良上人”,且诗歌后四句叙述,尤颇与佛家经义相关。“雨行江草短,露坐海帆稀”两句,是想象中“惟良上人”舟行“归润州”的情景,雨行、露坐苦行不止,作者敬佩之情深含其中。“正被空门缚,临岐乞解围”之结语,则是在说李端自己却又困惑苦恼,迫切需要“惟良上人”指点迷津,但现实却是上人归去,此时此地,空余别情……
中唐韩愈《感春五首,分司东都作·其一》诗云:
辛夷高花最先开,青天露坐始此回。
已呼孺人戛鸣瑟,更遣稚子传清杯。
选壮军兴不为用,坐狂朝论无由陪。
如今到死得闲处,还有诗赋歌康哉。
韩愈是反对佛教的,但恰是反对佛教的韩愈的这首诗,透露出或源于佛教之“露坐”仪式化的某些具体信息。“辛夷高花最先开,青天露坐始此回。”诗歌首联这样说,则表明,春回大地,辛夷花开,躲开了寒冬的肃杀,天气暖和了,又可以开始“青天露坐”了。这个诗例证实,至晚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之初,大唐的文士们早已形成了“露坐”的雅集传统,可以有音乐歌舞,可以传杯饮酒,可以写诗作赋。
唐宋时期,随着禅宗的兴起与文人禅悦之风的盛行,露坐已成为文人生活中常见的实践方式,为文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修行和艺术灵感来源。从佛教苦行到文人雅趣,既是一种修行方式,也是一种生活美学,更是一种哲学表达。
晚唐黄滔《秋思》诗曰:
碧嶂猿啼夜,新秋雨霁天。
谁人爱明月,露坐洞庭船。
黄滔的这首清新的小诗,好像并没有涉及个人遭遇与时代背景,但也可感受到一种难掩的忧郁与孤独。新秋雨霁,皓月当空,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,“露坐”孤舟,飘零无依,仿佛猿啼声声犹在耳畔。
以新秋、明月、猿鸣、行船等审美因素组合,黄滔还有另一首“露坐”诗。黄滔《送李山人往湘中》诗云:
汉渚往湘川,乘流入远天。
新秋无岸水,明月有琴船。
露坐应通晓,萍居恐隔年。
岳峰千万仞,知上啸猿巅。
北宋欧阳修《病暑赋》有曰:“飞蚊幸余之露坐兮,壁蝎伺余之入屋。”欧阳修赋作中的蚊虫,当然有可能暗指那些谗言中伤君子的“小人”,但显然欧阳修是知道“露坐”仪式的,且肯定也多曾进行过露坐。与他同时代的名士如蔡襄、曾巩、王安石、刘攽、韦骧等等则均写有“露坐诗”,有的还直接以“露坐”命题。如,刘攽便写有《夏夜露坐》诗,北宋蔡襄《四月池上》诗有曰:“风下平池水晕开,池边露坐水风来。”
孤独露坐,消解尘念,北宋曾巩《秋夜露坐偶作》诗有云:
喜兹宵漏初,露坐散襟抱。
河明带飞观,月白通驰道。
顾眄尘虑销,瓶泉谢频倒。
恨无同声人,诗义与探讨。
踟蹰拂方床,归卧梦亦好。
这样的“露坐”体验,好像是在呼唤“诗义与探讨”的“同声人”,坦然露出一种孤独无友或孤苦无依的状态,但其实这是一种文人的孤傲。如此“露坐”实质上是一种对抗世俗喧嚣的姿态,一种在静默中坚守自我价值的选择,所构建的是其高洁独立的精神世界,以抵御政治失意或现实困境带来的挫折。
北宋王安石《露坐》诗曰:
露坐看沟月,飘然风度荷。
珠跳散作点,金涌合成波。
老失芳岁易,静知良夜多。
陵秋久不寐,吾乐岂弦歌。
直接以“露坐”为诗题,作者又如此知名,王安石的这首《露坐》便应算作最著名的“露坐诗”了。
总体而言,露坐的意境营造主要体现在空灵、寂静与孤独的美学追求上;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或个人失意的时期,露坐成为了一种不屈服于外界压力、保持内心自由的精神姿态。
从佛教的“露地坐”到文人的“露坐”,从宗教苦行到诗意实践,在一片静谧中诗人完成了与万物外在、与自我心灵、与天地宇宙的对话。“露坐”仪式与“露坐诗词”,承载了唐宋以来中国古代士人复杂而深邃的文化心理,成为他们平衡理想与现实、调节内心与外界的重要媒介与方式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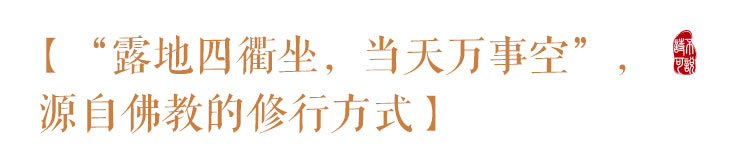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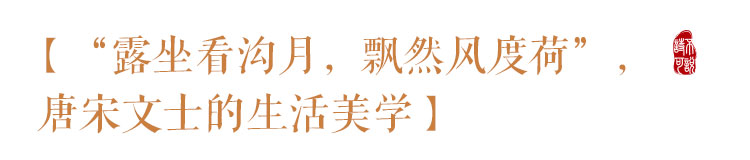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— 热门评论 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