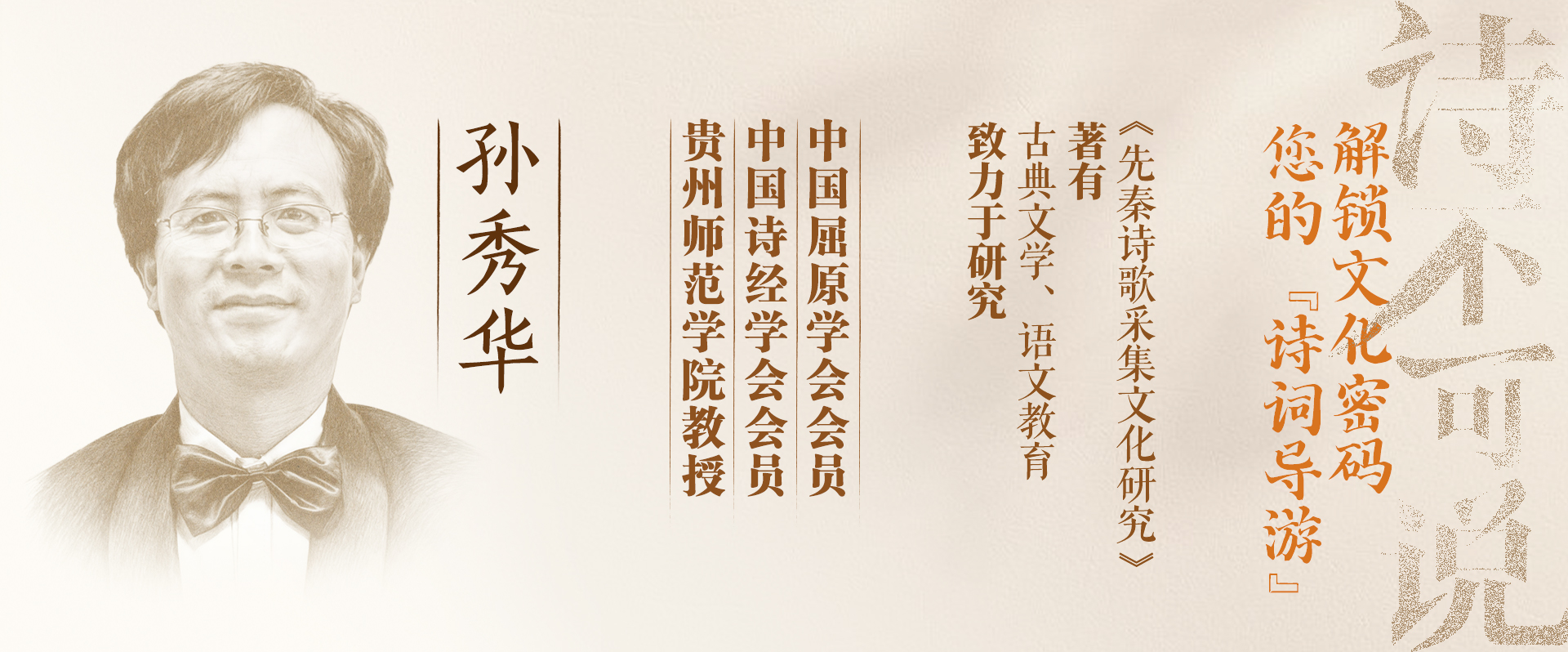
当我们轻吟宋代苏轼的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”,可曾想到,这雄浑壮阔的词调背后,竟然隐藏着一位盛唐顶流歌女的身影?是的,从词牌起源探微,念奴的传奇故事开启了《念奴娇》这一词牌的发展。
念奴,据信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歌女,曾多次为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演唱,并深受唐玄宗赞赏推崇。宋代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引述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载曰:“念奴者,有姿色,善歌唱,未尝一日离帝左右。每执板当席顾眄,帝谓妃子曰:‘此女妖丽,眼色媚人。’每啭声歌喉,则声出于朝霞之上。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。宫妓中帝之钟爱也。”这一记载认为念奴是“宫妓”,好像是有编制的皇宫歌舞团首席歌唱家,但据最早的讲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
最早的“念奴”传奇来自中唐元稹的诗作。元稹《连昌宫词》有云:
连昌宫中满宫竹……
上皇正在望仙楼,太真同凭阑干立。
……
夜半月高弦索鸣,贺老琵琶擅场屋。
力士传呼觅念奴,念奴潜伴诸郎宿。
须臾觅得又连催,特敕街中许然烛。
春娇满眼眠红绡,掠削云鬟旋装束。
飞上九天歌一声,二十五郎吹管逐。
逡巡大遍凉州彻,色色龟兹轰录续。
李谟擪笛傍宫墙,偷得新翻数般曲
平明大驾发行宫,万人歌舞涂路中。
连昌宫是一处大唐行宫,唐高宗显庆三年所建,故址在今河南省宜阳县。皇帝在行宫也能随心所欲地欣赏到念奴的歌唱,则念奴居然可以是“随驾”人员,这显而易见。诗句的大致意思是说,唐玄宗、杨贵妃在连昌宫,半夜歌舞正酣,乐师贺怀智弹奏琵琶。宦官高力士急忙传话,让歌手念奴出场,念奴此时却正与一位郎官共度良宵。好不容易才找到念奴,急忙接连催促她上场。甚至为了让念奴赶场,唐玄宗破例命人燃起烛火将她接来。原先睡在红纱帐里的念奴春心荡漾,娇艳欲滴。她稍稍整理了发型和装束后出场演唱。舞姿曼妙,恍若飞天仙子,高歌入云,二十五郎吹管伴奏,也仿佛跟不上节奏!念奴所唱,是整套的《凉州曲》,陆续还有各种龟兹曲调等等……
元稹生活的时代,距天宝年间仅有四五十年,他本诗中关于盛唐歌坛一姐念奴的这些歌咏,可信度自当是比较高的。更为难得的是,元稹对于念奴其人其事,还亲自作了注释。元稹自注曰:
念奴,天宝中名倡,善歌。每岁楼下酺宴,累日之后,万众喧隘,严安之、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,众乐为之罢奏。明皇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:“欲遣念奴唱歌,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,看人能听否。”未尝不悄然奉诏,其为当时所重也如此。然而明皇不欲夺侠游之盛,未尝置在宫禁。或岁幸汤泉,时巡东洛,有司潜遣从行而已。
结合诗歌内容与元稹的自注理解,则歌女念奴总是在盛大的皇家宴会上压轴出场,为她伴奏的是“二十五郎”,规模达二十五人的“管乐队”。但即便有二十五人伴奏,却也拦不住她的高歌声彻云霄。而尤为明确的是,按照元稹的说法,则念奴并不是“宫妓”,“明皇不欲夺侠游之盛,未尝置在宫禁。”
那么,“念奴娇”这一词牌是如何形成的呢?从音乐史的角度看,它最初应该是一支歌曲的名称,后来才固定为词牌。宋代王灼记载当时“音调飘逸,如此者皆慢曲也”,说明《念奴娇》在宋代已是一支旋律悠扬的慢曲子。而从“念奴”到“念奴娇”,多了一个“娇”字,或许正是对这位歌女艺术特质的精准捕捉——既有令人怀念的技艺,又有娇美动人的风采。从具体的歌手到抽象的音乐形式,从个人的艺术表现到普遍的文化符号,念奴的个人魅力被凝练为一种艺术形式,她的歌声穿越时空,在无数文人的笔下获得新生。
《念奴娇》词大部分作品为豪放词,在《念奴娇》词的创作史上,苏轼的《赤壁怀古》无疑是一座巍然耸立的巅峰,其雄姿英发、豪情万丈,直接影响辛弃疾、陈维崧等豪放词人的创作。念奴娇又有“酹江月”与“大江东去”等别名,词语直接来自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这也彰显了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巨大的影响力。
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词云:
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
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。
词作写于元丰五年(公元1082年),此时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已两年有余。政治上的失意、人生的困顿、世事的纷繁复杂,都在最后的“一尊还酹江月”里。苏轼已将个人的情感升华到宇宙境界——以江月为伴,与天地共饮,在有限中寻求无限,在瞬间中把握永恒——让我们每位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的生命沉思。
受苏轼影响,其后,宋代文人如黄机、黄革、周紫芝、高观国、张绍文、李好古等等均有填词《酹江月》;南宋叶梦得则写有《念奴娇·次东坡赤壁怀古》。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北传金国,金国文士蔡松年、王寂、赵秉文、段成己等人以《大江东去》为题的词作,留存约有二十首之多。
甚至,据《水浒传》,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还令宋江颇有感发,听了著名歌唱家李师师的演唱后,当场命笔填词一曲《念奴娇·天南地北》。《水浒传》第七十二回《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》写道:
……李师师低唱苏东坡“大江东去”词。宋江乘着酒兴,索纸笔来,磨得墨浓,蘸得笔饱,拂开花笺,对李师师道:“不才乱道一词,尽诉胸中郁结,呈上花魁尊听。”当时宋江落笔,遂成乐府词一首,道是:
天南地北,问乾坤何处、可容狂客?借得山东烟水寨,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围香,绛绡笼雪,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,薄幸如何消得?
想芦叶滩头,蓼花汀畔,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八九,只等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,忠肝盖地,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,醉乡一夜头白。
写毕,递与李师师反复看了,不晓其意……
呵呵,毕竟是小说家言。这首“宋江”的有感作文实在难与苏轼大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相提并论。自称狂客、买春之言、义胆包天、忠肝盖地等等,过于直白,甚至很是粗俗。结语又突兀写“离愁万种”,堆砌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,所抒写之苦闷,也离真正梁山英雄的义薄云天相去甚远。
而词史上,所确立的《念奴娇》词的“正体”居然不是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而是苏轼《念奴娇·中秋》:
凭高眺远,见长空万里,云无留迹。桂魄飞来光射处,冷浸一天秋碧。玉宇琼楼,乘鸾来去,人在清凉国。江山如画,望中烟树历历。
我醉拍手狂歌,举杯邀月,对影成三客。起舞徘徊风露下,今夕不知何夕?便欲乘风,翻然归去,何用骑鹏翼。水晶宫里,一声吹断横笛。
苏轼该作双调一百字,前片四十九字,后片五十一字,各十句四仄韵。以此苏轼《念奴娇·中秋》为“正体”,很显然可能是因为这一首更易于“填词”模仿,更适于当成典范。
总起来看,《念奴娇》属长调慢词,句式长短错落,韵位疏密相间,既有绵长悠扬的乐句容纳抒情,又有短促有力的节奏表现激昂,刚柔相济,适于融合个人情感与历史沉思,这种特质使得《念奴娇》作品往往能够超越具体情境,获得普遍的艺术感染力。
具体分析,超级歌星念奴极度优美的歌声代表着盛唐之音,那种恢宏的气象自然而然与后世文人的历史意识、家国情怀确有相通之处。而承接元稹的记载,在横空出世的天才苏轼手中,这个充满盛唐记忆的词牌注入了苏轼苏东坡自己的理想与感慨,完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,将对美好的追求、对历史的思考、对生命的感悟抒写到了极致。在这个意义上看,飞上九天歌一声,念奴与《念奴娇》的传奇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生动载体,是千年风流人物心灵世界的回响。每当我们吟诵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,不仅是在重温苏轼那豪迈而细腻的情怀,也是在延续念奴那悠远而传奇的歌声……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— 热门评论 —